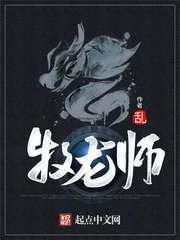三五中文网>朕真的不务正业 > 第九百九十六章 翰林院的文章 尽除空谈之风(第2页)
第九百九十六章 翰林院的文章 尽除空谈之风(第2页)
按照目前大明对拉丁文的了解,拉丁文是从希腊文演化而来。
文字的诞生,无论何处何地,最开始一定是壁画。
在翰林院翰林们看来,壁画是一种重要的文字,一种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,壁画也是文字的一种。
壁画逐渐转变为象形文字,象形文字最大的特点,就是像某种东西,比如牛就是真的画一头牛,比如甲骨文里祭祀的卯、伐、劓、刖、劅等等,每一个字都惟妙惟肖。
劓的甲骨文是一个挂钩一个人,人的鼻子挂在挂钩上;
而刖则是一个人和一条腿分开,中间有把刀;
劅的甲骨文,更加简单易懂,就是宫刑,去阴之刑,第三条腿,加上一把刀,就是劅。
象形文字的线条过于复杂,而且难以使用,在加上古代没有合适的记录工具,象形文字,一定会向有棱有角的楔形文字进行演绎,方便在石头、龟壳、青铜器上进行刻印。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而大明对甲骨文的研究,也佐证了这一点,越往后的甲骨文,也是棱角分明。
到了这个时候,一个字通常就会被人们赋予更多种的意义,在这个阶段,笔画也会出现。
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加方便的使用,初步具有了抽象意义的楔形文字,会逐渐趋向于简化。
而这一步,文字就会逐渐规范起来,造字、造词都变得有脉络可循,而文字也作为文化枢纽中的枢纽,维系着文化的大一统。
十里不同俗,百里不同音,虽然各地方言略有不同,但文字还是将大明完全缝合在了一起。
不仅仅中国发展脉络如此,海外商人带回来大量印加古国的金石器,这些文物刻画的都是最古老的文字,也是壁画、象形、楔形、表意表音的历史演变过程。
印加文明就属于典型的原生文明,有自己的原生文字,清晰的演变脉络,可是印加文明灭亡了。
印加文明符合原生文明的定义,这可能也是万士和万宗伯对印加古国的灭亡,念念不忘的缘故之一。
而翰林院翰林们在文章中,附录了一大堆文字来说明衍生文明的‘天残地缺’。
比如至今已经没有人能看得懂的契丹文、西夏文、女真文(北宋金文);还在使用中的朝鲜彦文、倭国的万叶假名;泰西的英文、葡萄牙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等等,这些全都是典型的衍生、派生文字。
这些天残地缺的衍生文字,使用有着诸多不便。
比如翰林院着重把宋辽金时代的辽国的官定文字契丹大字、小字进行了举例。
作为辽国的官文,契丹大字由辽国开辟之主耶律阿保机,仿照汉字所创。
但从创立之初,这种大字,就注定了无人使用,仿照创立,简直是多此一举。
辽国贵族、汉人都用汉文,尤其是辽国贵族以使用汉文为荣,对契丹大字不屑一顾。
唯一对契丹文字有需要的契丹底层穷人,他们又没有足够的精力,去学习这种大多数时候,完全用不上的契丹大字。
不得已,辽国为了推行契丹文,又创建了契丹小字,和朝鲜彦文、倭国万叶假名一样,契丹小字,是对契丹大字的注音。
表音文字最大的特点,是学习起来简单,可辽国科举、官文都用契丹大字和汉文,注定了这种表音文字在辽国倾覆后,变成了死文字。
契丹大字、契丹小字,在文字里,始终被归为了方言的存在。
西夏文、女真文都是类似的命运,辽国、西夏、金国存在的时候,这些文字就没有多少人使用,等到他们灭亡后,这种没人认得的文字,更多只是证明他们存在过的痕迹罢了。
朝鲜的彦文也有类似的命运,朝鲜贵族不用彦文,都用汉文,只有底层才需要这种表音文字,学来也没什么用,药典、法典都是由汉字书写,学了彦文、万叶假名这类的表音文字,一辈子都是穷民苦力。
原生文明的国格很高,贵族里的贵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