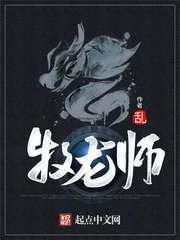三五中文网>风流俏佳人 > 第934章 角亢相照(第1页)
第934章 角亢相照(第1页)
<特别鸣谢:tijin送出的大神认证,特此加更!>
却说杨炯被尤宝宝以银针封了腰眼要穴,正自苦笑不迭,求饶未果之际,忽闻客栈外更鼓声声,已是定更时分。
杨炯猛地想起今夜之约,只得暂且按下腰间那若有若无的酸麻之感,换上一身玄色锦袍,虽非王侯规制,却也针脚细密,暗绣云纹,透着几分内敛的贵气。又将那早已备好的狭长礼盒珍而重之地负在背后,盒中所盛,正是他承诺赠与辽国新帝耶律倍的宝刀。
收拾停当,杨炯便去寻尤宝宝。
尤宝宝虽恼他口无遮拦,却也知今夜之事非同小可,见他来寻,只冷着脸哼了一声,到底还是跟了上去。
两人出了客栈,融入了析津府的夜市人流之中。
此时华灯初上,六月的析津府,夜风仍带着白日的余温,却也拂去了几分燥热。
长街两侧,店铺鳞次栉比,幌子高挑,竟大多以契丹文、华文双语书写,什么“善记绸庄”、“宋记皮货”、“脱脱马鞍”,灯火辉映,人声喧阗。
贩夫走卒,引车卖浆,契丹贵人高车驷马,华族商贾步履从容,间或还能见到身着异域服饰的西域胡商、高丽使臣,端的是五方杂处,繁华似锦。
尤宝宝自幼长于南方,也见过长安气象,此刻也不禁微微颔首,轻声道:“都说辽国彬彬无异于大华,今日一见,果真如此!你看这市井繁华,人烟阜盛,言语互通,衣冠杂糅,若非这些契丹文字与胡人面貌,几疑是回到了长安西市。”
杨炯目光扫过街景,应道:“辽人立国已久,与我华族纠缠争斗数十年,早非昔年逐水草而居的部落。他们效仿我朝制度,兴科举,劝农桑,建城郭,如今亦是耕战读书,样样不差。这析津府作为南京,更是其菁华所在。”
尤宝宝听了,秀眉微蹙,叹道:“我在长安时,常听那些太学生议论,说华辽之间,终有一战,可是真的?似这般各自安生,百姓乐业,岂不更好?”
杨炯引着尤宝宝转入一条稍显清静的街道,沉吟片刻,方沉声道:“天下大势,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。战与和,有时并非一厢情愿。眼下两国皆经大战,元气未复,彼此都需要喘息之机,互为倚仗。至于将来……谁也难以预料。”
尤宝宝本是医者,心地纯善,于这等军国大事并不甚了了,见杨炯似不愿深谈,便也乖巧地不再多问,转而将被路边一卖糖人儿的小摊吸引了目光,笑着凑上前去,拣了一个憨态可掬的玉兔捣药形状的,付了钱,拿在手中把玩,又递到杨炯嘴边让他尝。
杨炯见她有意活跃气氛,心下莞尔,配合地咬了一口,那糖稀的甜意在舌尖化开,暂时代替了酒宴的期待与隐忧。两人便这般有说有笑,穿街过巷,倒像是寻常人家夫妻夜游一般。
行不多时,眼前豁然开朗,乃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小湖,湖畔垂柳依依,一座三层楼阁临水而立,飞檐翘角,气派不凡。
檐下悬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,正是“醉天仙”三字。
此时楼内灯火通明,丝竹雅乐隐约可闻,进出之人多是身着儒衫的文士或是一些低品级的官员,看来是个雅致的去处,不似寻常喧闹酒肆。
杨炯整了整衣袍,拉着尤宝宝刚至门前,便见一个身着绫罗、体态富态的中年胖子快步迎上。
这人生得面团团一张脸,未语先带三分笑,一双小眼睛却精光闪烁,显得极为精明干练。
他快步走到近前,并不高声,只微微躬身,执礼甚恭:“贵人可是姓杨?我家主子已在三楼雅间等候多时了,特命小人在此迎候。”
言语间,目光在杨炯背后的礼盒上飞快一扫,神色愈发恭敬。
杨炯知是耶律倍安排的心腹,略一点头。
那胖子也不多话,侧身引路,带着二人避开大堂喧嚣,沿着雕花木梯蜿蜒而上,直抵三楼。
三楼更为清静,走廊尽头有一处角落,胖子在门前停下脚步,垂手肃立,示意便是此处。
杨炯深吸一口气,推开房门,拉着尤宝宝迈步而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