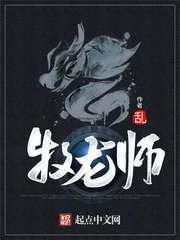三五中文网>我在古代考公,商家子的赶考日常 > 第403章 你做成了,我保你;你做砸了,与我无关。(第3页)
第403章 你做成了,我保你;你做砸了,与我无关。(第3页)
赵成梁微微颔首,眼底闪过一抹赞许,却很快隐去。
“工匠做事,需要工具,也需要…避开风浪的眼线。
老夫在这河上看了几十年,哪里水缓,哪里礁石林立,
哪段河道归哪个衙门管,哪个吏员认得几斤几两…
这些旧舆图,或许还有些用。”
说着,他将一本看似普通的《漕运纪略》推到了林向安面前。
书页泛黄,但里面可能夹着只有他才懂的特殊标记,或是某几页做了注解。
老伯爷递给林向安的书,实际代表着立场,不能明着支持,但可以给林向安提供最关键的情报。
如何打通漕运和京城关卡的关系网,哪些人是可以收买的,价格几何。
“工匠辛苦,酬劳自然不能少。”
赵成梁抿了口茶,淡淡道:
“水引进来,按市价买卖,天公地道。
只是这‘市价’…如今这光景,该如何定,是个学问。
定高了,渴死的人多,怨气冲了堤坝,不好。
定低了…工匠们白忙一场,寒了心,
以后就没人肯做这卖命的营生了。”
这是同意协助运粮赚钱,但不能赚黑心钱引发民变。
要找到一个既能覆盖成本风险、又能稳定人心,
还能让我们都满意的‘公道价’。
这个度,让林向安来把握。
林向安心领神会,立即拱手道:
“老伯爷放心。工匠们求的是长远生计,非一时暴利。
所定之价,必以能养活工匠、维系渠道为先,
继而惠及坊间殷实人家,使其能购得活命之水,
如此,市面不至大乱,工匠亦能得利。
其中分寸,晚辈必谨守慎行。”
这一番回答,点明价格会略高于平日,以涵盖风险成本与利润,但远低于黑市,重在维稳,让各方皆得其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