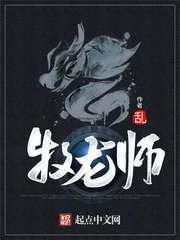三五中文网>锁情扣 > 第366章 番外 华天佑和赵灵儿(第4页)
第366章 番外 华天佑和赵灵儿(第4页)
起初,只是些零星的猜测。皇后娘娘自年前便称病静养,各种场合都未曾露面,这本身就极不寻常,就连“皇宫教室”的讲课也突然停了下来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流言如同春雨后的野草,疯狂滋生,版本繁多。
有说皇后娘娘其实早已病入膏肓,药石罔效,陛下情深,不肯面对,才一直秘不发丧。
有说皇后娘娘是触怒了上天,因她传播的那些“异端邪说”,遭到了天谴,昏迷不醒。
更有人说陛下在未央宫修建冰室,并非为了静养,而是用以保存皇后娘娘的……玉体,使其不腐。此等逆伦悖德之事,实乃骇人听闻,有伤国体。
也有嗅觉敏锐的,探听到恒国公世子华天佑与赵灵儿原本定于三月初一,却毫无征兆突然推迟的婚事,更是佐证了“国丧”的猜测——若皇后并未薨逝,陛下最宠爱的妹妹出嫁,何以会无限期推迟?
“听说啊,宫里如今一点喜庆颜色都不见,宫女太监走路都踮着脚尖,生怕触了霉头。”
“可不是吗!我家那口子在衙门里当差,说上头的大人们一个个都小心翼翼的,不敢提半个‘喜’字。”
“陛下这般……岂不是因私废公?皇后若真的……那也该按照祖制办理后事,如此不明不白,算怎么回事?”
“嘘!慎言!你不要脑袋了?陛下是什么脾气?当年在苍州,那可是杀伐决断的主儿!”
各种流言蜚语,如同无形的潮水,在京城每一个角落涌动。不敢欢笑,不敢嫁娶,不敢大肆宴饮,整个京城,仿佛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罩住,失去了往日的活力,变得死气沉沉。
这股暗流,终于不可避免地涌向了朝堂。
这一日的朝堂上,气氛格外凝重。
在处理完几项常规政务后,一名年约五旬、身着绯色官袍的御史,手持玉笏,声音洪亮却带着谨慎:“陛下,臣有本奏。”
赵樽高坐龙椅,目光平静地扫过去,是御史台的老臣周御史。以耿直敢谏闻名,但也有些迂腐。
“讲。”
“陛下,”周御史深吸一口气,似乎下定了决心,“皇后娘娘凤体违和,静养已久,臣等与天下百姓,皆忧心忡忡,日夜祈盼娘娘凤体安康。然,娘娘久未现身,致使坊间流言四起,多有揣测不恭之语。长此以往,恐伤国本,动摇民心。臣斗胆恳请陛下,若娘娘凤体已然康复,可否择机让娘娘露面,以安天下之心?呃……若娘娘凤恙仍未痊愈,也请陛下明示,以免小人揣度,滋生事端。”
这番话,说得可谓委婉至极,既表达了关切,又点出了流言的危害,最后将选择权交给了皇帝,无论皇后是康健还是病重,只要有个明确说法,就能平息风波。
然而,龙椅上的赵樽,面色没有丝毫变化,只是眼神微微冷了几分。
他还没开口,又一名大臣站了出来,是礼部的一位侍郎,语气比周御史更直接了些:
“陛下,周御史所言极是。国有大事,当明告天下。皇后娘娘乃一国之母,母仪天下,其安康关乎国运。如今民间因不知宫中确切消息,以至于不敢婚嫁,不敢庆贺,长此以往,礼乐不兴,民间怨怼暗生。臣恳请陛下,为江山社稷计,早定章程。”
紧接着,又有三四位官员出列附议,那言辞或恳切,或激昂,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。那就是皇后娘娘到底怎么样了,陛下您给句准话吧!
朝堂之上,一时之间,劝谏之声此起彼伏。
不少耿直的老臣都觉得,陛下此举,于情可以怜悯,但于理确实不合,于法更是有亏。
皇后若真已薨逝,按照祖制,就该举行国葬,天下服丧;若只是生病,也该让御医或有威望的宗室命妇探视,以证视听。
如今这般隐匿深宫,以冰保存身体,实在是旷古未闻,匪夷所思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站在朝臣前列的恒国公,虽然没出列说话,但他也眉头紧锁,眼观鼻,鼻观心,心中忧虑重重。
他担忧自己的儿子华天佑,同时也担忧陛下。
华天佑与长公主灵儿的婚事推迟,他并无怨言,毕竟若皇后真有不测,作为臣子、作为好友,守制是应当的。他只怕陛下这般执拗,会引来更多的非议,甚至影响朝局稳定,也会令华天佑和赵灵儿的婚事出现无限期的等待。
他偷偷抬眼觑了觑龙椅上的赵樽,只见对方面沉如水,看不出喜怒,但那股无形的低气压,已经让熟悉他性格的恒国公心中暗叫不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