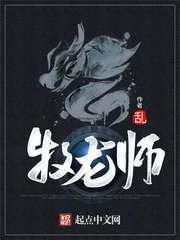三五中文网>大明:当了三年圣孙,称帝六十载 > 第979章 治国之道,用人之道(第2页)
第979章 治国之道,用人之道(第2页)
暖阁内一片沉寂。
只有自鸣钟的咔哒声和窗外隐约传来的宫人脚步声。
朱翊钧端坐在宽大的御座之上,明黄的龙袍衬得他面沉如水。
他没有立刻说话,只是目光越过申时行和张学颜,投向窗外那片澄澈高远的秋日晴空。
那六万多名稚童的身影,仿佛穿透了千山万水,浮现在他的眼前。
他们穿着粗布短褂,带着田野的气息,坐在那些新起的、或许还散发着泥腥味的学堂里。
他们可能还懵懂无知,可能还会因为想家而哭泣,可能还会在先生的戒尺下瑟缩……
但他们的父母,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,此刻心中必定燃烧着一丝微弱的、名为“希望”的火苗。
朝廷管饭,朝廷教认字!
这是千百年来,压在底层百姓身上那沉重的、名为“绝望”的巨石,第一次被撬开了一道缝隙……
朱翊钧叹了口气,这个时代的自己,即便贵为天子,可能对百姓做的事情,也并不会太多。
听着申时行的奏报。
朱翊钧想起了海瑞。
那个执拗的老头,现在想必,定是会感到欣慰……不过,若是现在还活着,能够亲眼看看,更能让人欣慰。
海瑞去世虽然一年多了,但他在朝堂的影响力,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,并没有减少。
特别是北方的诸县,如今竟村村都有了海瑞祠。
在这一年多中,百姓自发捐钱捐物,把庙宇修得比乡祠还气派,每日香火缭绕,有县令在呈文里说,寒冬时节,海瑞庙的门槛都被祈愿的百姓踏平了,香火钱竟足够赈济镇上的孤寡,成了当地一道奇景……
朱翊钧前些时日,去大兴县,还专门去了一趟海瑞庙,当真是修的气派。
朱翊钧也从各地的奏报中得知,在以往他为官的地方,几乎都i有海瑞庙的存在。
淳安的海瑞生祠原本只是间小庙,如今被百姓扩建成三进院落,门口的石碑上刻满了近些年捐银百姓,乡绅的名字。
应天府的百姓更是把海瑞疏浚过的河道称为“海公河”,河边的祠堂里,四时八节都有船家供奉的河鲜与香火。
而在,海瑞的老家自发建起了南方最大的海瑞庙,乡绅们牵头,百姓们义务出工,庙宇落成那日,据说半个海岛的人都去了,香火绵延十里,连路过的商船都要停船祭拜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朱翊钧缓缓收回目光,落在申时行和张学颜身上。
他的眼神深邃如古井,看不出狂喜,也看不出丝毫的志得意满。
只有一种沉甸甸的、如同背负着万钧重担的凝重。
“六万人啊。”
“这是主官的功劳,也是满朝诸公的功劳……”
“这,只是第一步。万里之行,方始于足下……”说着,朱翊钧看向满殿的重臣轻声叹息道:“辛劳诸公,在加把劲了。”